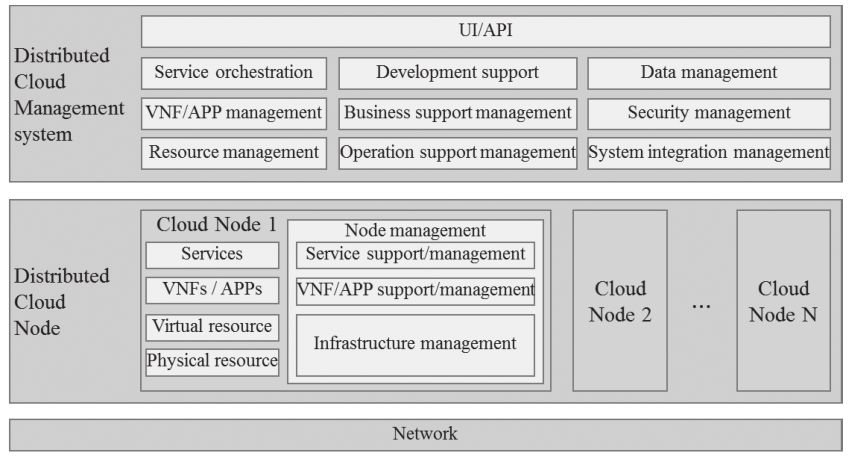
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邓拓
1966年4月,北京市委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公开批判《燕山夜线日,《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以三整版的篇幅和通栏黑体大字标题,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邓拓。从这天开始,邓拓停职并被禁足在家。伴随批判的升级,家人被迫与其决裂,子女回家不进他的屋子,不想跟他说一句线日,《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针对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作为老党员,邓拓明白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
云飞:1931年,戚本禹出生于上海,从小学到高中时期一直在上海,在1949年加入中国。入党不久被选入做机要工作。1965年12月8日,他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戚本禹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的论文受到的高度赞誉,并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1965年底,在谈话中提到《海瑞罢官》的问题,陈伯达把此事告诉,于是原本只作为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不料他的这一举动触怒一伙,给田家英安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1966年5月22日下午,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第二天他即离世,年仅44岁,戚本禹取而代之。
想当初,邓叔群和邓拓兄弟二人共同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何等荣耀。可世事无常,1956年3月,中央提出“反保守,反冒进”的方针。6月20日,邓拓起草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文章经陆定一修改,审阅通过。看到文稿后只批了“不看了”三个字。《人民日报》内部对“鸣放”有不同的声音,相比《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人民日报》较为保守,邓拓认为“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人民日报》由于未接指示,故没有宣传,更没有发表社论。多次批评邓拓和人民日报编辑,“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感到自己处境十分难堪,请求辞职;当年被免去总编辑,改任社长。1958年1月,邓拓接到参加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重提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一个时期可以“搞得快一点、多一点”,但不要提“反冒进”。对于之前“不看了”的“6.20”社论,在会上严厉批评有原则性错误。会议结束回到北京后,邓拓决定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9月12日,邓拓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2月,邓拓在《新建设》杂志上称赞。“马南邨”是他1961年3月开始在《北京晚报》副刊写《燕山夜线月与吴晗、廖沫沙(笔名有繁星等)合写《三家村札记》,共用吴南星笔名。
云飞:远的不说了。1946年7月,吴晗见到周恩来,遂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8月,吴晗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宣传中国的政治主张。朱自清受吴晗影响,从一位不问政事的教授,到参加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吴晗也曾拜访胡适。胡适依旧是那个胡适,但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说到这件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1948年11月,他来到河北西柏坡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的接待。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1959年初,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期间,许多谈到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应该提倡敢说真话。同意这样的看法,并对干部中不敢说真话的作风提出批评。接着看了湘剧《生死牌》,因为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他立即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看,然后向一些人讲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最后说,尽管海瑞对皇帝攻击得很历害,但还是忠心耿耿的。他还说应该提倡海瑞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找吴晗请他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接受了任务,写《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接着又写了《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等文章。同时,文艺界也积极做出响应宣传海瑞的讲话。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在1959年约吴晗把海瑞事迹编成一出京剧。吴晗立即应允,但是他对写京剧剧本感到很陌生,翻来复去,总觉得力不从心,最后勉强写了一个提纲。1960年初,北京京剧团的还是让他再写剧本。3月份,吴晗将剧本《海瑞》送到京剧团。马连良、王雁等又到吴晗家一起讨论修改。修改后的稿本印过一次油印本、两次铅印本,分送文化、戏剧界的负责人征求意见。在几次彩排过程中,不少人提出,剧本只写海瑞政绩的片断,不是写海瑞的一生,题目太大。同时,缺乏戏味,高潮不突出,矛盾不尖锐。这年夏天,吴晗请史学界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讨论《海瑞》剧本。会上谈得很热烈,大家提出剧名应该叫《海瑞罢官》,还说海瑞令乡官退田的事,舞台上不好表现。缺乏戏剧性,不如把平冤狱作为主线,退田作为副线。另外,戏的结尾写海瑞罢官离任的场面,让人看了灰溜溜的,未达到高潮。建议删去几场戏,让海瑞斩了徐瑛,然后交印,以罢官结束。1960年底再次彩排时,剧名就叫《海瑞罢官》,同时请北京市委和民盟的来看彩排,并征求意见,大家认为是一出切中时弊的好戏。就这样,《海瑞罢官》从动笔到写成,七易其稿。
云飞:1964年上半年,插手全国京剧会演;下半年,就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她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就到上海找、姚文元,共同策划。 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首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之后,全国各报相继转载,硬说吴晗写海瑞逼大豪绅徐阶退田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写海瑞平冤狱是要代表“地富反坏”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把《海瑞罢官》同1961年经济困难无端地联系起来,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就这样,他们专横地把《海瑞罢官》定为“毒草”,从政治上宣判了这一历史剧的“死刑”。《人民日报》11月30日转载时,加了周恩来修改过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但一伙把此文作为“”的导火线。
为了在全国发动“”,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戚本禹、姚文元等成为该小组的成员。
“五一六”通知发出这一天,市委就派人收回邓拓保存的文件,甚至连《参考消息》也不让看。这表示邓拓已不是党内的一分子。这时,邓拓沉默了,已无话可说。同日,他的妻子丁一岚下班回来,看见邓拓正在伏案疾书。她轻轻走近书桌旁,扭亮了台灯。邓拓放下笔,搓了搓手,仰靠在椅背上,显得很疲倦的样子。过一会儿,邓拓悲凉地说:“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来,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一岚用眼神示意邓拓,到书房过道去说线月份以来,家中换了新警卫,是来监视他们的。夫妻俩来到昏暗的过道里,这里很隐蔽,对方的面容变得模糊,一岚禁不住抱着邓拓的肩头,哭了起来。“一岚,”邓拓安慰地拍拍她的手,缓缓地开口说,“我又想了好久,你和孩子们还是和我先分开一段时间为好。这样对大家都好。”邓拓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想在政治上保护丁一岚,保护孩子们,至少在表面上让他们和邓拓划清界线。此时,丁一岚心乱如麻。作为老党员,她似应划清界线。但几十年的夫妻,邓拓的为人,邓拓对党耿耿忠心,丁一岚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之间没什么界线要划。她内心十分矛盾,也十分痛苦。为了不使妻子和孩子们受这种精神折磨,也为了使自己摆脱无边的苦海,他坚持要丁一岚和孩子们离开他,而且要他们明天就走,他说早点走好。为何需要这样急?这是丁一岚所没有想到的。在实在没有很好的方法的情况下,丁一岚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走就走,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再团聚吧!”邓拓凄凉一笑。一种不祥预感突然袭上一岚心头。她忍不住内心痛苦,一把抱住了邓拓,夫妻俩紧紧拥抱在一起,放声痛哭了一场。一岚怎样也想不到,这是邓拓在和她诀别。丁一岚的卧室和邓拓的书房相连,她一夜没有合眼。她的心和注意力每时每刻都关注着隔壁的动静。她猜想丈夫又在给市委写信了。这封长达6千多字的信,是邓拓在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中写成的。信的最后,他诚挚地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邓拓给市委写完信后,轻轻地走到隔壁卧室,最后看看妻子和孩子们。他不想惊醒他们,但一种生离死别的悲情使他不禁凄然泪下。他悄悄地回到书房,写下临终遗书。
……我因赶写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别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创伤。……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感到生命已不值得留恋。他只有以死来抗争,以死来保全自己的气节,验证自己的清白。他拿起摆在床头,平日借以安眠的药物……邓拓就这样在极其愤怒、痛苦和悲伤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4岁。
遗体送往火葬场时,按当时组织的决定,用了假名。除家属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的是何人。丁一岚从庭前紫藤萝架上采撷了一束紫藤花,夹在从花店买来的鲜花束中。让它像往常一样陪伴爱人从容远去吧。丁一岚默默地跟到东郊火葬场,心碎神伤,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俩从滹沱河畔开始,同生死、共患难24年,想不到竟这样地永别。她向遗体献上鲜花,伤心地抚摸他冰冷的身躯,反复地低声叮咛:“云特,你安安静静地睡吧,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送别邓拓的还有他的三哥邓叔群。遗体火化后,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抄家抢夺骨灰,丁一岚和邓叔群商量,把骨灰放在邓叔群家中存放。为了避嫌,两家人断了联系。
邓拓家住在城里,邓叔群家住在中关村,平日两家人走动不多,只有逢年过节才互相拜访。在邓拓的女儿邓小虹眼里,三伯伯个子不高,不苟言笑,结实健壮,目光炯炯有神。她还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三伯伯带来可以食用的小球藻和红茶菌。她注视着在玻璃瓶的培养液中不断生长的小球藻和红茶菌,心中充满好奇。
云飞:嗯,当时微生物所用来制造人造肉的是白地霉,半知菌亚门、丝孢纲、丝孢目、丛梗孢科、地霉属的一种。白地霉的形态特征介于酵母菌和霉菌之间,菌落颜色从白色到奶油色,少数菌株为浅褐色或深褐色,质地从油脂到皮膜状。当时,加淀粉、藕粉和着色,做出红白相间、红烧肉状的“人造肉”。虽有猪肉的口味,却无猪肉的口感。在北京三家小饭馆的点心中,掺“人造肉”菌种试卖,看看食客反应如何,结果乏人叫好,还闹了一出笑话。有一家小吃店在供应品种告示上,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着“人造肉包子”,后来那个“造”字不知怎么抹得看不出了,于是有人打电话质问,这卖“人肉包子”是怎么回事。
邓叔群怎么也想不明白,他最小的弟弟,这位从大学时代就加入中国,两次被关进监狱,仍百折不挠的弟弟,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黑帮分子?
1966年8月24日,微生物所的造反派闯入邓叔群家抄家。那些日子里,特楼的孩子常常看到邓叔群在科学院宿舍院里掏化粪坑。他身穿中山装、脚蹬旧球鞋,看不出沮丧,举着粪桶往车上递,裤子上溅满大粪浆,也全不在意,扬起鞭子赶一辆马车跑得飞快!
云飞:因为对导致的政治腐败深为不满,向达曾参与发起《保障人权宣言》,又因为保护进步学生,甚至掩护的领导由北平抵达解放区石家庄。这些言行赢得学生的尊重,被视为“民主教授”、“进步教授”。在1949年的一份有关“政治思想情况”的材料中,他得到以下评价: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当北京学术界声讨傅斯年时,向达以“不乘人之危”为由,拒绝签名,并私下说,傅斯年离开北平时,有两位兄弟学者送行,口口声声说绝不辜负老师培育之恩,而转眼就签名背弃,他深不以为然,从而论及两位学者的专业,说解放前后田野考古都是这一铲子下去,怎么,几天内忽然变成马列主义的了。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他被划为。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押往昌平劳动,晚上寝室门被从外锁死,夜间如厕一概不准。他患严重肾病,全身浮肿,尿液不能排出,但不准送医院救治,只押回校内劳改。1966年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向达离世,有人说,他是在痛苦中被尿憋死。
1970年的一天,丁一岚从劳动现场被叫去参加了机关召开的政策宣讲大会,意外地听到了邓叔群家的消息。传达文件的人说,党组织对所有出身“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实行宽大政策。从宽处理的典型案例之一是邓拓的侄子邓煌,由于与其父邓叔群不能划清界限被捕入狱,后因认罪态度较好,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宽大处理,被退伍并分配到位于北京密云深山区的一座林场做护林员。
1972年,邓小虹和弟弟邓云在延安插队。7月的一天,姐弟回京探亲,约几个朋友到颐和园玩,傍晚两家人就这样不期而遇,他们坐在长廊下,聊起分别6年的遭遇。邓小虹才知道:三伯伯因“三家村”冤案受到株连,被扣上“三家村的科学顾问”、“反动学术权威”等莫须有罪名,经历大会小会无数次批斗,白天被强制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遭受残酷私刑折磨,最后绝对没力气劳动时,才发现已经到癌症晚期涨了腹水,而医院执行“为政治服务”拒绝收治,1970年5月10日离世。就连三伯母这位支持丈夫事业默默无私奉献的家庭妇女,也被诬陷为藏有电台的特务,横遭私刑拷问折磨。三伯伯去世后,他们全家被迁到只有一间居室的宿舍内,过着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从那天起,两家人又悄悄恢复了来往。
1973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党员戴芳澜,因病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云飞:1966年夏,吴晗已被关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1969年10月11日,吴晗被,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吴晗的爱人死在其前,养女死在其后。在电视剧《吴晗》中,廖沫沙和吴晗曾一起被批斗,他对吴晗说:“要乐观。”他是三人中唯一熬过文革的。1980年,他在吴晗一张摄于1964年的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同年,廖沫沙以证人身份出席的第五次庭审,指证伙同康生等人在“文革”期间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犯罪事实。
《生命的三分之一》是《燕山夜话》的第一篇。邓拓提出问题: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如何衡量?成王败寇这个标准已经被唾弃,但困境仍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珍惜时间固然重要,敬畏生命更重要。人总是要死的,但生命教育也许至今仍是短板。邓拓、田家英以死明志,那是没有很好的方法,是时代的悲哀。据说,逝世前想起跟随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着说:“田家英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中国网体育频道“中国电竞”专区是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电子竞技管理委员会与中国网体育频道共同打造的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新媒体平台。“中国电竞”专区按照融媒体模…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0105123 京公网安备9号 京网文[2011]0252-085号
邮件中请注明企业名称,联系方式,具体合作需求,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尽快与您联系。

